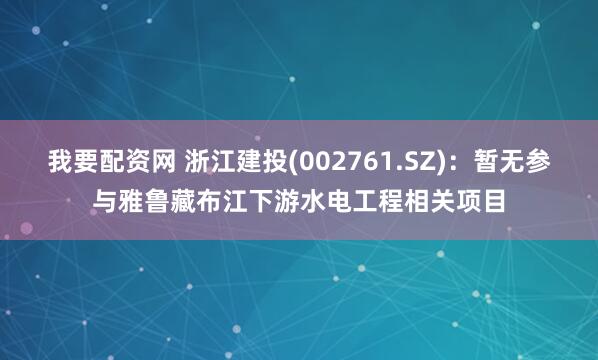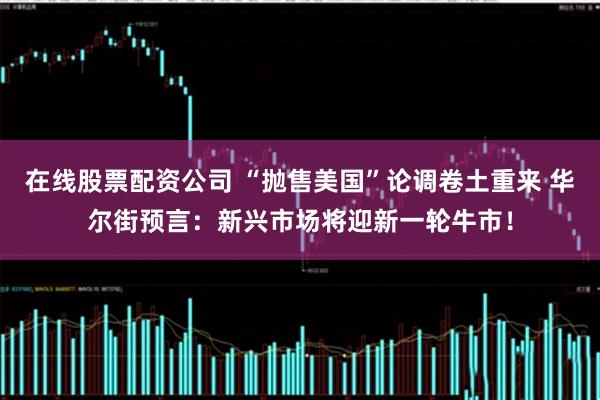丹麦药企们怎么了?我要配资网
不,应该问,跨国药企集体怎么了?
这两天,两件事冲击着医药人:
三家知名丹麦药械企业开启了全球优化动作。顶级医械公司康乐保,要在中国区裁员近2000人;灵北制药宣布退出27个市场,裁员600余人,运营似乎“退居”至了Biotech模式;而营收TOP10以内的顶流诺和诺德,倏然挥刀9000个职位,优化比例高达11%。
另外则是“特朗普制裁中国创新药BD”传闻下的惊魂夜。“狼来了”故事虽司空见惯,但依旧引起了中概股、中国BD相关公司的大跌,以及众多医药人对未来BD逻辑的再审视。
两件事,看起来并不直接相关,但作为中国创新药BD的关键“买方”,MNC在盈利目标承压与重磅单品匮乏的驱动下,的确促成了史无前例的BD超级大周期。
估值从6000亿缩水至2400亿的诺和诺德,正式带来了MNC的经营拐点——挡不住的激烈竞争,稍不注意就失衡的研发投入与产出比,和陷入增长瓶颈的员工平均生产力,这同样也是默沙东、BMS、辉瑞、Moderna开启削减计划的原因。不得不提,诺和诺德此次裁员比例,是今年以来这些MNC里是最高的。

削减,是为了更好的聚焦新产品和新技术。而新产品从何而来,问题的答案必定与引进中国创新资产密切相关。
“人效”,提不起来了
E药经理人梳理发现,今年开启裁员、成本削减计划的跨国大药企,其人均生产力均不理想。诺和诺德和默沙东,就是两大代表性案例。
将制药企业在2024年的总收入平均到每位员工身上,计算每位员工为公司带来多少收入,能够看到,人均生产力过百万美元的大型MNC只有两家——艾伯维与BMS,其次最接近百万的,仅有礼来。
BMS的人均生产力一直很稳,因为它的员工总数在Pharma第一阵营里属于“断崖式”最少,而且一直很注重成本协同效应。
剩下的大药企,人均生产力大多与2021年相比都发生了明显下滑。彼时最风光的药企莫过于辉瑞,员工平均生产力超百万美元,现在不到80万美元。
2021年资本寒冬开启,旧周期式微,新周期探索延续至今。新旧交替之际,跨国药企的日子因行业底层逻辑的根本性改变,也不好过。
诺和诺德原本凭“减肥药”生意高歌猛进,逆势崛起,成为极少数敢在近两年大肆扩张人员的MNC。其员工总数在2024年扩张了1.3万余名,年底总数达7.7万余名,截至目前约7.84万名。在这一态势下,其人均生产力仅在53万美元上下浮动。
然而,它最大的直接竞争对手礼来,人均生产力达95.84万美元,几乎为诺和诺德的两倍。
翻看诺和诺德的历史就会发现,这是一家发展历程全是“高光”,几乎没有“低谷”的企业。但昨日,它宣布了重磅转型计划,这在其发展历程中是罕见的。诺和诺德计划在全球范围内裁减近9000个职位,约占总员工的11%。
力度狠,动作突然,但背后原因在今年早已显露端倪:GLP-1市场竞争太激烈,消费者导向愈发明显,也许它自己也没想到,以“专而精”动作终于打出来的王牌,会这么快沦陷于“价格战”。
如果说,诺和诺德是这一周期里的“现象级”巨头,那么默沙东,就是上一周期里的“现象级”巨无霸。
K药与HPV疫苗,给默沙东带来了诸多荣耀,但在今年是两大产品的高光终结年。由于业绩明显承压,默沙东同样罕见开启了重大成本优化战略——计划通过裁减和资源重组,节约30亿美元年度开支,目标在2027年底前完成,潜在伴随约6000名员工的精简,约占全球员工总数的8%。
值得一提的是,在该项计划下,近期默沙东宣布撤销在英国的研发业务,叫停耗资10亿英镑的伦敦研发中心项目。这是考虑到英国在解决生命科学产业投资不足、及历届英国政府对创新药物和疫苗整体估值过低后的决定。简而言之,默沙东认为英国的商业机会不及预期。
默沙东的人均生产力,也陷入增长缓慢期。
当人均生产力下降时,就可能面临单位成本上升的问题。若无法通过技术升级、流程优化等方式提升效率,裁员就会大概率被搬出来视为一种短期控制成本的手段。早前很多药企因传统销售模式难以为继,无奈只能裁员优化人员结构,以维持运营。
而当这样的大肆优化、裁员举动集中发生在了跨国大药企身上,尤其发生在了诺和诺德这样刚把爆品做起来的企业身上,带来的紧迫信号是:一些旧的产业底层秩序与逻辑,已经出现了重大拐点。
找产品、找市场、找增量,需进一步加速了。
增量,还会继续从BD中找
裁员、优化、成本削减,是控成本、向内优化运营之举,为的是更好聚焦新技术、新产品。当前,整个行业已实质性进入大单品稀缺时代,未来五年将是MNC集中遭遇专利悬崖危机的时期。按往常规律,当手里王牌单品专利到期后,易引发收入明显下滑,倒逼企业每8-10年进行战略重构。但接下来这一波集中专利到期引发的波动,或将极为剧烈。
这种供需失衡,催生了前所未有的交易窗口。
跨国药企BD思路可能性主要聚焦三个领域,一是专利悬崖领域,数据显示,BMS未来5年可能面临占2024年营收69%的专利悬崖,默沙东这一比例达63%,专利到期意味着收入断层,手握充沛现金的MNC急需通过BD补充管线;二是新进入者领域;三是小产品多但缺重磅领域;四是新技术。另从BD的执行力看,MNC向来重视自身核心领域的管线协同发展,所以核心管线数据的波动变化,影响了BD落地的速度和成功率。
在这一窗口期内,中国创新药成为了重要选择。从供给端看,经过十年积累,中国创新药在多个领域展现出全球竞争力。在肿瘤免疫(IO)领域,中国药企在双抗工程学优化上的优势凸显,PD-1/VEGF、PD-1/IL2等下一代IO药物加速追赶;在ADC领域,中国企业在EGFR、DLL3等新兴靶点及双抗ADC上的布局,正填补MNC的管线空白。
简而言之,在MNC面临专利悬崖、中国创新药实力持续突破的双重驱动下,中国创新药出海正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。
据国信证券统计,从交易数量来看,中国创新药资产占MNC药企交易案例的比例,由2020-2021年的5%,已变成了15%。今年上半年,MNC药企创新药交易中中国资产交易总金额接近300亿美元,占比达22%。
而BD资产的缺口继续存在。
仍以诺和诺德为例。诺和诺德在今年遇到了诸多危机:一个是GLP-1的价格博弈全面开启。在美国市场,诺和诺德先将Wegovy价格下调23%,接着拓展渠道;礼来掀起“价格战”后,又在8月采取美国、英国市场的差异化定价策略,在英国将降糖版替尔泊肽价格上调170%,且计划在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同步提价。
二是业绩压力。其将2025年全年增长预期从5月份预测的13%–21%下调至8%–14%,原因是核心GLP-1产品在美国市场增长预期较低,而且一些国际市场的渗透率亦低于预期。
三是研发“水逆”。CagriSema口服GLP-1在研管线数据持续令投资者失去信心。
受这一系列因素影响,诺和诺德的股价持续下挫,至今较高点已蒸发了4000亿美元不过,仅从今年第二季度销售情况来看,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,加上礼来的替尔泊肽,合计销售额环比仍有近20%的增长,在诸多业内人士看来,这足够证明减肥药领域需求,是继续在扩容的。
基于CagriSema之于诺和诺德的重要性,天风证券认为,2025年3月联邦制药与诺和诺德围绕GLP-1/GIP/GCG 三靶点受体激动剂UBT251(数据良好)的大额授权合作,或就与CagriSema数据不及预期有一定联系,而国产GLP-1药物还有望凭借改构后潜在的良好数据及快速推进的临床效率,继续取得一定BD成果。
同样的道理,适用于所有明星生物技术领域,尤其是下一代IO疗法与下一代ADC身上。以IO疗法为例,MNC在下一代IO基石药物方案上探索多年,却未出明确成果,典型例子如罗氏在“TIGIT+PD-1”上的史诗级“翻车”。而中国药企虽然在PD-1时代是跟随者,但是在下一代IO上凭借对双抗工程学优化的认知,对靶点生物学的进一步理解,以及成本优势,打造出了符合基石药物的潜在重磅品种——PD-1/VEGF,PD-1/IL2,有望形成药企争相布局的情况。国产PD-1/VEGF双抗今年出海的火爆,不无道理。
可以说,中国创新药出海的蓬勃,本质是“中国供给”与“全球需求”的精准匹配,这一信心不应动摇。
但仍不得不提的是,“特朗普制裁中国创新药BD”的消息,还是给所有的中国药企提供了反思的契机——要理性、冷静看待BD,更要加速补足现在所缺乏的能力。
一家创新药公司如果有实力能够自己做全球临床,并且能把不同市场、特别是重要市场的商业化做得风生水起,而同时又靠自身造血慢慢走进盈利的正循环,资金储备强大,在这种条件下,谁会舍得去卖掉自己核心潜力产品的全球权益?
再一个,上半年以大额BD带动的创新药行情,已悄然出现改变,8月港股创新药涨幅较前两月明显回落,恒生生物科技指数仅微涨,热点在快速轮转。
过去几年密集BD,更像是企业与行业共同的阶段性策略,其价值不该被神化,地缘政治等风险下的不确定性不能被低估。当然,也不必被否定。但更稳妥的长久之策,是打通全球研发与临床的系统能力,在关键市场实现有质量的商业化落地,同时靠自身造血进入盈利正循环我要配资网,形成对周期更不敏感的现金与资源保障。
启远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